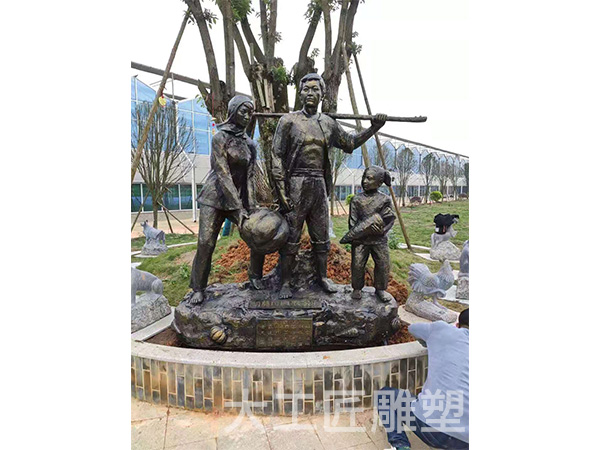雕塑材料的三個基本向度
- 發布時間:2021-09-24
- 發布者: 本站
- 來源: 原創
- 閱讀量:
與其他藝術門類不同,雕塑對材料的依賴性更強。誠然,藝術家的所有藝術只有通過物質材料才能表達出來,物質材料是雕塑藝術的載體。但是,對于普通觀眾而言,一幅國畫畫在紙上或者絹上,使用廣告顏料還是傳統國畫顏料,其區別度遠不如作者畫的是男人還是女人那么大。而雕塑則不同,一件作品使用石頭還是金屬,在視覺上的區別就非常明顯。此外,對一件雕塑作品的欣賞,通常還可以通過觸摸完成。在觸覺上,材質的光滑與粗糙,都能通過神經纖維末梢傳達到大腦,大腦再做出反應。宋偉光指出 :“不同質地的材料其自身的物理性質所呈現出的視覺效果和觸覺感受各不相同。對藝術家來說,材料是一種語言,當被藝術家所采用時,它便顯現出了其性格。”1 從材料角度來看雕塑藝術的觀念表達、情感傾注與語言呈現,也許更為有趣。
盡管雕塑家許正龍說 :“世界上沒有不能利用的材料,關鍵在于人們是否發現材料的美并能充分把它表現出來。”2 但是,藝術家對于雕塑材料的選擇是受時代、地域、經濟能力、顧客口味等因素的限制的,尤其受到社會集體觀念的影響。
秦代李斯泰山刻石(拓本)
在中國古代,那些由上層階層主導制作的帶有紀念性的雕塑,其材料主要是金與石。前者主要是青銅,也包括其他金屬 ;后者包括了玉一類的名貴石頭。以金屬作為雕塑材料,主要取決于冶煉技術的提高,它相比石頭作為材料的歷史要晚很多。不過,這兩種材料的穩定性遠遠超過了人類的個體生命,普遍都被視為長壽的象征。《古詩十九首》中的“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表達的都是這種意思。對那些不關心個體生命長短而志在建立功業的人來說,以金石材料制作器物,能體現出對于“永恒”的追求,正如《呂氏春秋》中所說 :“功績銘乎金石,著于盤盂。”對于木、泥這類固定性不強或者易朽的材料,如果要用來制作雕塑作品,通常都與死亡有關。面積 2.5 萬余平方米的秦始皇陵兵馬俑,出土的 7000多個真人大小的將士雕塑,都以泥為材料。遍布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漢墓,其陪葬俑也幾乎皆為木質或者泥質。這一觀念一直延續到作為明器的唐三彩,同樣也是以泥為最初的材料。與此相應的是,用來記錄死者事跡的墓志,則都用堅硬的石頭制作。它似乎在表明這樣一種觀念 :即使是在死后世界繼續使用的陪葬俑,也有其生命的長度,而主人的功績銘刻在石頭上,則可以與天地一樣長久。
北洞山漢墓彩繪陶俑
使用何種材料來制作沒有實用功能的雕塑,也反映了藝術家或者贊助者的等級觀念。所以,凡是皇家或者貴族資助的雕塑,都采用名貴罕見的材料 ;而常見的木材、普通的石頭或者粗糙的泥料所制作的雕塑,通常都在下層民眾之間盛行。巫鴻說 :“中國古代的青銅禮器,包括珍貴的禮儀性玉、陶器,實際上都在‘浪費’和‘吞并’生產力。”3 從這句話來理解古代雕塑,可以認為中國古代在材料的使用上是有階層性的。因為雕塑所用的所有的材料,幾乎同樣也可以用來制作生產工具或日用品。大量的可以用于改善普通民眾日常生活以及提高生產力的材料,都被用于制作那些體現上層統治者身份地位的紀念性雕塑,說是“浪費”和“吞并”,并不顯得偏激。
清代民間供奉的木雕神像
今天,新材料、新技術不斷出現并被運用于雕塑中,其背后的觀念更值得玩味,比如玻璃鋼材料在二三線城市廣場雕塑中大量出現、生態雕塑對于可持續性強和易降解的新興材料的追求、數字雕塑中無須藝術家直接接觸的虛擬材料等等。可以說,不論人類有多少種觀念類型,都能通過雕塑所使用的材料歸納出來。
材料本身沒有情感,是藝術家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了其中,材料才成為藝術品的有機構成,從而引起觀者的共鳴。對材料與情感的認知,實際上是對“情”與“物”二者關系的認知。20 世紀以來,西方美學與藝術理論話語主題發生了轉變,藝術表現論成為主要議題。傳統的主體和客體二元對立的模式,被主客二體統一模式所替代。阿恩海姆的情物同構說提出主客體統一的共同基礎是力的結構,客體對象因具有力的式樣而有表現性和趨同性 ;杜夫海納的情感先驗說則認為主客體統一的共同基礎是情感先驗,審美對象因具有情感性質和意向性特點而成為“情感物”或“準主體”。無論是阿恩海姆還是杜夫海納,都注重藝術家與藝術作品之間的主客體的互動關系。
亨利·摩爾作品之一
海德格爾強調 :“世界本身不是一種世內存在者。但世界對世內存在者起決定性的規定作用,從而唯當‘有’世界,世內存在者才能來照面,才能顯現為就它的存在得到揭示的存在者。”4人定義了世界,并與世界構成聯系,從而獲得存在感。因此,站在人與世界之外來看世界是沒有意義的。藝術歸根結底是人的藝術,藝術因人而存在,因為人賦予了藝術以情感。雕塑亦是如此。
亨利·摩爾作品之二
舉例來說。一般的觀者初次看到摩爾成熟期的石雕,可能會誤認為這是從某處直接搬運過來的天然石塊。自然界的一塊石頭,經過千萬年的風吹雨刷,在形態上確實可能會接近于摩爾的某件作品。但是,即使再逼肖于摩爾,擺在公共場合也只是一塊石頭,而不會成為藝術品。摩爾在石頭上做了技術上的加工處理,但更多的是投射了他的個人情感。摩爾把他對于母子之間的情感理解,轉化為一個可視可觸的形體。這個主題升華之后,母與子不只在人與人之間存在,同樣也可以表現為人與自然的情感——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與人也是母與子的關系。
在藝術生涯的后期,摩爾通常將自然環境與雕塑作品作為一個整體來構思。正如摩爾自己所解釋的那樣 :“將人像與風景交織在一起,正是我在雕塑中試圖要做到的。這暗示了人類與大地、山峰以及自然風光的內在聯系。如果用詩意的語言來描述,那山巒的起伏正像羚羊那輕快的一躍,而雕塑本身就像詩一樣充滿了隱喻。”5 石頭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在材料上,摩爾只需要改變其物理形態。對于另外一類青銅作品,摩爾則采用腐蝕劑來改變材料的化學性質,安置在常綠樹木周邊的雕塑,通常披上了一層淡淡的綠銹。其目的也在于達到雕塑作品與環境色彩的協調,不至于讓觀者產生情感上的沖突。
純粹從藝術語言的角度來創作和研究雕塑的歷史并不長。西方雕塑家對于雕塑語言的探索要稍微早一點。美國學者威廉 · 塔克的《雕塑的語言》一書,總結了羅丹、畢加索、馬蒂斯、布朗庫西等藝術家的獨特的雕塑語言,并從雕塑本體出發,最終指向他對現代雕塑所做出的明確界定:“雕塑作為自我包含的物體。”6我們在解讀羅丹的雕塑《巴爾扎克》時,往往傾向于去分析羅丹出于什么原因將巴爾扎克塑造成這個形象,此時的巴爾扎克正在構思哪一部小說。欣賞一件佛教雕塑時,會去考證這是魏晉的還是隋唐的,是什么人發愿制作了它。諸如此類,仿佛除去題材本身之外,我們對一件雕塑就不知道應該談論什么。當遇到摩爾或者布朗庫西的作品時,觀眾完全不懂得這是在表達什么。雕塑本體語言成為橫亙在雕塑家與普通觀眾之間的一道溝塹。對于普通觀眾而言,雕塑語言是一門外語。通過視覺與觸覺的雙重感知,我們至少知道一件作品采用的是石材還是金屬——雕塑語言是一種可以理解的外語。
山東日照沙雕
構成雕塑語言的兩個最核心的要素是空間和材料。實事求是地說,當代已經有許多中國雕塑家意識到了語言對于雕塑本體的重要性,也在自覺地探討如何拓展雕塑語言。殷雙喜指出,包括軟材料及日常生活現成品在雕塑中的運用,“推動了富有人文精神特質的新藝術的生成。”7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一些雕塑家為了標新立異,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忽視對空間的探討,一味地嘗試傳統雕塑中很少用的新材料,比如紙、皮革、毛發、布料、棉花、塑料、野草、玻璃、藥丸、藥渣、空瓶子、硅膠、包裝盒、冰塊、水等。在很多雕塑家看來,對制作材料的過度追求,最終會使得作品淪為工藝品。石村批評這些“挖空心思去尋找奇異的材料”的藝術家是“本末倒置”。8
由于空間的探索更加考驗雕塑家的智力與耐力,反而被年輕雕塑家所忽視。單獨來看,不管是傳統的金石竹木,還是新興的玻璃纖維或者碳纖維,都只是一種普通的物質,雕塑家通過對它的三維形體進行規劃確定之后,形成一種占據空間的形體,它才成為雕塑語言的一部分。所以,一直致力于雕塑空間探索的朱尚熹說:“雕塑的最為重要的精神指向,其實就是以實在物質形態的形式,哺育和啟迪人類的空間維度心智,順帶承擔點宗教、政治、審美的義務而已。”9
哈爾濱冰雕
雕塑尚未出現于人類社會的時候,制作雕塑的材料就已經存在于自然界了,雕塑依賴于材料而生。但是,將雕塑與材料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個學術問題來探討,尚不到一百年的歷史。隨著科技的發展,各種合成材料仍舊在源源不斷地產生。因而對于雕塑材料本身的實驗并未終止,雕塑家對于材料如何表達觀念、傾注情感與呈現語言的探索也不會結束。材料對于雕塑藝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如以宋偉光的這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吧 :“雕塑史若從媒材的角度審視,那么它便是一部材料史,每一次對新材料的運用都會帶來對雕塑藝術新的探索,甚至是藝術變革。”10(原文載于《中國雕塑2019》)